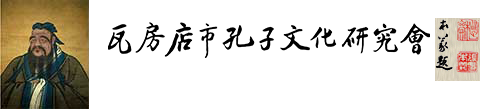试论佛教伦理与道教伦理的“儒学化”
2011-01-07 浏览348次
摘要:古中国有儒释道“三教合一”之说,但三教实际上又不可等量齐观。就伦理道德层面的功能与作用而言,佛教和道教确实是不可与儒教比肩的。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,便在伦理道德上自觉地选择了“儒学化”这一路径。道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,其走向与佛教基本上如出一辙,即在伦理道德上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“儒学化”的道路。佛教伦理和道教伦理的“儒学化”,主要体现在阐述忠孝思想作品的撰写、忠孝思想的提倡、戒律与“五常”的会通、以忠孝作为宗派立教之本等方面。
关键词:佛教伦理;道教伦理;儒学化;忠孝
本文标题所说的“儒学”,指的是由孔子创立、由后儒继承和发展的儒家的思想学说。一般认为,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,是以一直有“儒家”之称。但作为表现中华民族固有价值系统的儒家,又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,因为儒家似乎又是一种宗教。在有的学者(如康有为、蔡元培、陈汉章、贺麟、张岱年、任继愈、李申等)看来,儒家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,但却具有宗教的功能与作用,故可称之为“儒教”①。笔者的判断是,大致而言,称“儒学”为“儒教”,自有“其持之有故,其言之成理”者(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)。因此,出于行文和讨论的方便,本文对这三个称谓不作严格的区分。
古中国有儒释道“三教”之说,但三教实际上又不可等量齐观。就逻辑的严密性、思辨的抽象性而言,儒学实有不如佛学者;就对民间社会的影响而言,道教似乎尚强于儒教,以致鲁迅有“中国的根祗全在道教”的说法[1];但就对政治制度、伦理道德的影响而言,佛教和道教实又全然不可与儒教同日而语。换句话说,儒家特别强调道德的自觉和道德的作用,着力挖掘伦理规范(伦常)的社会功能,特别注重对仁、义、礼、忠、孝等伦理道德规范的申说(“留意于仁义之际”),视伦理道德为维系家庭、社会、国家的根本原则。因此,儒学是修身之学、实践之学,伦理道德学说构成了儒家学说的核心和灵魂,故儒学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[2]。这是儒家的看家法宝之一(古人早已如此视之②),也是儒学在中国源远流长、代代相传且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原因之一。毫无疑问,儒教的这一功能和作用,确实是佛教和道教所不可替代的。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,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,便在伦理道德上自觉地选择了“儒学化”这一路径③。道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,其走向与佛教基本上如出一辙,即在伦理道德上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“儒学化”的道路。
佛教伦理的“儒学化”
作为“异质文化”的佛教,无论是在价值观念上还是在行为规范上,都与华夏民族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。因此,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,随即面临着“冲突-融合”这一难题。尤其是佛教宣扬众生平等、出家修行、超越名教等(典型者如沙门不敬王者、不礼拜父母),与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度、宗法制度、伦理道德形成了尖锐的对立。
通过早期的《牟子理惑论》④,我们可以看到,佛教和儒家在伦理道德观念上的分歧,很大程度上便集中在忠、孝两大问题上(印度佛教尽管也提倡尊敬父母,但“孝”在其中并不居于重要地位)。六朝以降,佛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,特别注意将儒家的忠、孝思想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。东晋时期,慧远(334-416)从理论上沟通了佛教伦理学说与儒家政治伦理的关联⑤,一度缓和了儒佛之间的矛盾。但终乎唐朝之世,儒佛的冲突仍然非常激烈(韩愈的反佛、唐武宗的灭佛便是明证)。宋朝之时,契嵩(1007-1072)又援儒入佛、会通儒佛,在伦理道德上全面调和佛教与儒家,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矛盾。其后,佛门代代都有致力于此者,使“三教合一”成为中国文化鲜明的风景线。
佛教界阐述其忠孝思想的著作,为数其实并不少。在《法苑珠林》中,释道世(?-683)专设《忠孝篇》、《不孝篇》和《报恩篇》、《背恩篇》来阐述佛教的忠孝观和恩义观(分别见《法苑珠林》卷四十九、卷五十)。大约在唐朝初期,中国高僧专门撰写了一卷《父母恩重经》(《开元释教录》卷十八),作为佛门孝道观的经典,这也是佛教伦理“儒学化”的典型作品。其后,又由此演绎出《父母恩重经讲经文》、《十恩德》、《十种缘》、《孝顺乐》等佛曲、变文和变相。北宋之时,出现了契嵩“拟诸《孝经》,发明佛意”的《孝论》,极力宣扬“戒孝合一”说,这是佛教关于孝最为系统、最为全面的著作,故契嵩在历史上有“一代孝僧”的美誉。其后,宋僧宗赜(1053或1054-?)著有《劝孝文》,而在其《苇江集》中宣传孝道的文章竟有一百二十篇之多。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智旭(字蕅益,1599-1655),也撰写了《孝闻说》、《广孝序》等重要文章。当然,敦煌佛教文献是其大宗,故潘重规说:“等到敦煌石室开启,文献资料渐渐流布,我们才看清佛教徒提倡孝道的事实,他们力量之伟大,影响之深远,方法之周密,实在令人钦佩赞叹。”[3]
在思想上,佛教由原先的不拜父母、不尽孝道,转而宣扬孝道,主张换一种方式对父母尽孝(有别于儒家)。《佛说父母恩难报经》云:“父母恩惠,无量无边,不孝之愆,卒难陈报。”契嵩说,“道”是“神用之本”,“师”是“教诰之本”,而“父母”是“形生之本”,三者是“天下之大本”(《孝论·孝本章》),故当对父母尽孝。准此,契嵩又提出了“孝为戒先”说,“夫孝也者,大戒之所先也。戒也者,众善之所以生也”(《镡津集》卷三《辅教编下·孝论·明孝章》)。他将孝分为不可见的“孝之理”和可见的“孝之行”,“理也者,孝之所以出也;行也者,孝之所以形容也”(《镡津集》卷三《辅教编下·孝论·原孝章》)。故他认为,佛教徒虽然遁入空门而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奉养父母,但在父母去世后仍尽三年心丧,“三年必心丧,静居修我法,赞父母之冥”(《孝论·终孝章》)。契嵩的三年心丧之说,显然与儒家不同;因为儒家行三年心丧的对象是老师,而不是父母(见《礼记·檀弓上》)。智旭将孝提升到佛教根本宗旨的至上地位,“儒以孝为百行之本,佛以孝为至道之宗”(《题至孝回春传》,《灵峰宗论》卷七之一),“世出世法,皆以孝顺为宗”(《孝闻说》,《灵峰宗论》卷四之二)。又,儒家关于孝有这样的说法,“立身行道,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,孝之终也”(《孝经·开宗明义章》)。在契嵩看来,佛教徒以出家修行的方式立身行道,同样可以荣宗耀祖,使祖先亡灵得到福报。智旭将孝分为“世间孝”和“出世间孝”,世间孝“以喻亲于道为大”,而出世间之大孝则“发无上菩提心,观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皆我父母,必欲度之令成佛道”(《孝闻说》)。因此在他看来,佛教的“大孝”远远超过了儒家的“大孝”。我们完全可以说,佛教的这些孝道思想既是对儒家孝道思想的继承,同时也是发展,并且还有所超越。
佛教徒进而认为,佛教的戒律本和儒家的伦理不相矛盾,实可圆融无碍。其最典型者,当数以“五戒”与“五常”的比附与会通。“五戒”指的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,这是佛教最基本的戒规,是对佛教徒行为的约束。“五常”指的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“谓之五常,言可以常行之也”(柳宗元《时令论下》)。
早在佛教传入中土的初始期,就有人认为佛教的“五戒”可以比附儒家的“五常”,“又有五戒,去杀、盗、淫、妄言、饮酒,大意与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同,名为异耳”(《魏书·释老志》)。北齐著名思想家颜之推(531-约590)晚年由儒学而归心佛门,他同样认为“五戒”可与“五常”相沟通,“内外两教,本为一体。渐极为异,深浅不同。内典初门,设五种禁,外典仁义礼智信,皆与之符。仁者,不杀之禁也;义者,不盗之禁也;礼者,不邪之禁也;智者,不酒之禁也;信者,不妄之禁也”(《颜氏家训·归心》)。宋僧契嵩进一步认为,“五戒”实可会通“五常”,并且突出了孝道,“夫不杀,仁也;不盗,义也;不邪淫,礼也;不饮酒,智也;不妄言,信也。是以五者修,则成其人,显其亲,不亦孝乎?……夫五戒,有孝之蕴”,“五戒”与“五常”实际上是“异号而一体”(《镡津集》卷三《辅教编下·孝论》),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别。而且在契嵩看来,佛教的“六度”(指使人由生死轮回之此岸到达涅槃寂灭之彼岸的六种法门,即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精虑/禅定、智慧/般若),其宗旨亦与儒家“五常”殊途同归,“儒所谓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者,与吾佛曰慈悲、曰布施、曰恭敬、曰无我慢、曰智慧、曰不妄言绮语,其为目虽不同,而其所以立诚修行、善世教人,岂异乎哉”(《镡津集》卷八《杂著·寂子解》)。言下之意,“五戒”、“六度”虽与“五常”名目不同,但同样是为了修身养性、劝善去恶。在佛教徒的视野里,佛教甚至在最为宽泛的层面上也是大有裨益于家庭与社会、国家与政治的。唐朝高僧释道宣(596-667)在在强调,“惟佛之为敎也,劝臣以忠,劝子以孝,劝国以治,劝家以和”(该语分别见于《广弘明集》卷十四和《法苑珠林》卷六十八)。契嵩认为,佛教“治心”、儒教“治世”,同为“圣人之教”,“其所出虽不同,而同归乎治”(《镡津集》卷八《杂著·寂子解》)。
就宗派而言,禅宗(以南宗为主流)是最为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之一,在理论上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、“即心即佛”、“顿悟成佛”;在修行上提倡“世间即出世间”,认为在现实生活中遵循纲常名教并不妨碍修习佛法。六祖慧能(636-713)所造《坛经·疑问品》云:“心平何劳持戒,行直何用修禅。恩则孝养父母,义则上下相怜,让则尊卑和睦,忍则众恶无喧。……听说依此修行,天堂只在目前。”禅宗学者宗密(780-841)以其博综三教的渊博知识,竭力统一儒释道三教的思想,旗帜鲜明地提出“禅教一致”论。其中,宗密又特别强调了孝道,“始于混沌,塞乎天地,通神人,贯贵贱,儒释皆宗之,其唯孝道矣”,“经诠理智,律诠戒行。戒虽万行,以孝为宗”(《佛说盂兰盆经疏》卷上)。
为了显示自己对孝道的重视,佛教还把孝的宣传纳入佛事活动;最典型的活动之一,便是“盂兰盆会”⑥。而与之相关的“目连戏”(以“目连救母”故事为题材的戏剧),在民间更是颇为盛行⑦。“盂兰盆会”及“目连戏”之所以盛行不衰,绝非偶然因素所致,关键在于它宣传了孝子的孝行。在佛教雕刻艺术中,我们也可以看到孝的画面。在四川大足石刻中(宝顶山第十五龛),有一组“父母恩重经变”群雕(计有《佛前祈嗣》、《怀胎守护恩》、《临产受苦恩》、《生子忘忧恩》、《咽苦吐甘恩》、《推干就湿恩》、《乳哺养育恩》、《洗濯不净恩》、《为造恶业恩》、《远行忆念恩》、《究竟怜悯恩》等十一组石刻作品),便以宣扬儒家孝道为主题,以其具体而生动的艺术形式宣扬了儒家的孝道观念。
现代大德印光法师(1861-1940)认为,佛教和儒家的伦理道德相资互补,和衷共济,“尽性学佛,方能尽伦学孔;尽伦学孔,方能尽性学佛。试观古今之大忠大孝,与夫发挥儒教圣贤心法者,无不深研佛经,潜修密证也。儒佛二教,合之则双美,离之则两伤,以世无一人不在伦常之内,亦无一人能出心性之外。具此伦常心性,而以佛之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,为克己复礼、闲邪存诚、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之助。由是父子兄弟等,相率而尽伦尽性,以去其幻妄之烦惑,以复其本具之佛性。非但体一,即用亦非有二也”。(《复安徽万安校长书》,《增广印光法师文钞》卷二。)
自从太虚大师(1889-1947)等在民国时期倡导“人间佛教”以来,经过八十余年的探讨、实践、弘扬,也已获得佛教界和社会的赞可与认同,成为当今海峡两岸佛教界共同高扬的旗帜,被誉为“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最可宝贵的智慧结晶”[4]。在笔者看来,在伦理道德上走“儒学化”的道路,当是“人间佛教”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由此可以看出,“儒学化”是中国佛教伦理最突出的特征,即中国佛教伦理认同和接受了儒家的纲常伦理。虽然说中国佛教伦理在中国伦理道德的长河中并非主流,但它确实丰富了我国优良的传统道德,因此也是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。
道教伦理的“儒学化”
道教与儒教“冲突-融合”的情形,与佛教有几分相似,但又不如佛教那么激烈和尖锐;毕竟,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。而与佛教相同的是,道教在伦理道德方面也走上了“儒学化”的道路。同时,道教又吸收了佛教的不少东西(包括在伦理道德方面)。
面对佛教的挑战,道教徒也撰写了《太上真一报父母恩重经》、《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》、《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》、《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父母成道经》等着重阐述孝道的经典。另外,在《太平经》、《抱朴子内篇》、《太上感应篇》、《劝世归真》、《十诫经》、《玉清经》等诸多道教典籍中,宣扬忠、孝以及仁、信、礼等的文字也是随处可见。
在道教的早期经典《太平经》中,对忠、孝的宣扬可以说是不遗余力。比如,“夫天地至慈,唯不孝大逆,天地不赦”[5]116,认为不孝是大逆不道、天地不容。又比如,“人生之时,为子当孝,为臣当忠,为弟子当顺;孝忠顺不离其身,然后死魂魄神精不见对也”[5]408,认为忠孝乃天经地义,不可须臾离身;相反,“子不孝,弟子不顺,臣不忠,罪皆不与于赦”[5]406。《太平经》甚至认为,“为不顺忠孝之人,罪皆及其后”[5]685-686。
早期道教经典《老子想尔注》也讲忠、孝、仁、义、诚,“人为仁义,自当至诚,天自赏之,不至诚者,天自罚之”,“臣忠子孝,出自然至心”,“臣忠子孝,国则易治。……既为忠孝,不欲令君父知,自嘿而行,欲蒙天报”[6]。
在《抱朴子内篇》中,道教理论家葛洪(283-363,一说284-364)更是一再强调行善立功是成仙的重要条件,认为儒家道德(忠、孝、仁、信等)的修炼是成仙的前提和保证。如《抱朴子内篇·对俗》说:“按《玉钤经中篇》云,立功为上,除过次之。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,护人疾病,令不枉死,为上功也。欲求仙者,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。若德行不修,而但务方术,皆不得长生也。”[7]葛洪从而把道教教义与儒家名教纲常结合起来,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道教的本来面目。
其后,北魏的道教领袖寇谦之(365-448)在崇信道教的北魏太武帝(423-451年在位)和宰相崔浩(381-450)的支持下,全面改造五斗米道,“宣吾新科,清整道教,除去三张(按:即张陵、张衡、张鲁)伪法、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”;在改造的过程中,寇谦之便吸收了儒家的礼法思想,“专以礼度为首,而加以服食闭炼”(《魏书·释老志》),主张臣忠子孝、夫信妇贞、兄敬弟顺,信守五常(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)(《老君音诵戒经》)。由于寇谦之的改造适应了当时的需要,所以大受魏太武帝的赏识,被授予“天师”、“国师”的桂冠。
由王喆(1112-1170,号重阳子)创立的全真道(又称全真教),主张三教合一,认为三教本来同源,“儒门释户道相通,三教从来一祖风”(《诗·学道示人》,《重阳全真集》卷一)。在立教经典上,全真道以《道德经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为主要经典。王重阳教育在家修道者要恪尽伦常之道,“与六亲和睦,朋友圆方,宗祖灵祠祭飨频,行孝以序思量”,“忠君王,孝顺父母、师资”(《重阳全真集》卷五)。全真道特别强调,忠君孝亲是修炼性命的基本外功,而不孝、不敬和不善之人是不准参加全真道的。
南宋初年创立的净明道,其说以“本心净明”为要,力主“行制贵在忠孝”(《玉真刘先生语录》,《净明忠孝全书》卷三)。净明道直接以“八宝垂训”(忠、孝、廉、谨、宽、裕、容、忍)⑧作为其教义的主要内容,并突出强调忠、孝,“净明只是正心诚意,忠孝只是扶持纲常”(同上),故自称“净明忠孝道”。这体现了净明道伦理型宗教的特点,同时也是道教伦理“儒学化”的重要体现。
道教劝善书《劝世归真》认为,人既成其为人,天然地应当尽忠尽孝,“人生在世,莫忘忠孝二字。为臣尽忠,为子尽孝,乃万古不易之理也。吾劝世人,或为忠臣,或为孝人,则不愧为人矣”。《劝世归真》的这种论说方式,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儒家《孝经》的说法。《孝经·三才章》说:“夫孝,天之经也,地之义也,民之行也。”两相对照,二者如出一辙。为了有效发挥道教戒律的规约作用,《劝世归真》还借文昌帝君之口,专门开出了“治人心病良方”,“忠直一块,孝顺十分,仁义广用,信行全要,道理三分,阴骘多加;好肝肠一条,慈悲心二片,温柔四两,仔细十分,公道全用,和气一团,小心一个,忍耐十分,恩惠多施,方便不拘多少,安分一钱,老实一个。以上十八味药,宽心锅内炒,不要焦,去火性,平等盆内研碎,三思罗兜筛过,波罗密为丸,如菩提子大。每日不拘时服用,和气汤送下。切忌背理、两头蛇、暗中箭、笑里刀、肚内毒、平地风波。只此六件,务须要勤戒。人若难寻此药材,汝心桥下肚家开,不用银钱拿去买,回心铺内觅将来。此方专治男女不忠不孝,不仁不义,不恭不敬,亵渎天地圣贤,明瞒暗骗,害众成家,利己损人,刁唆词讼,妄捏是非,逞凶横行,欺贫陷富等症。依方修合,可以延年益寿、灭罪消灾、一生安稳,永保百世其昌”。“治人心病良方”中的一些用语,如“慈悲心”、“波罗密”、“菩提子”等,明显来源于佛教;而其提倡忠、孝、仁、义、信等,则无疑来源于儒家。但道教的这种做法,全然是宗教式的,而与儒门教化之旨判若天壤。有的学者说,“道教这种说教比之儒家伦理,似乎具有更为强大的作用力”[8],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或许如此。
约成书于北宋初年的《太上感应篇》认为,“欲求长生”,当避恶行善,其中多有与儒家伦理相吻合者。比如,“父母为五伦之首,孝亲乃人道之先”,“忠孝友悌,正己化人;矜孤恤寡,敬老怀幼”;不得“抵触父兄”,不得“违父母训”,不得“背亲向疏”,不得“失礼于舅姑”,等等。《太上感应篇》谆谆劝导世人,“立善多端,莫先忠孝”,“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”。附带说明的是,《太上感应篇》不但吸收了儒家思想,同时又吸收了佛家思想(连文字都相同)。如佛典《法句经》卷下云:“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,自净其意,是诸佛教。”
敦煌道经残卷《十诫经》所谈训诫有与“五伦”相对应的规定,并且广及忠、孝、仁、信、礼等伦理范畴。如:与人君言则惠于国,与人父言则慈于子,与人师言则爱于众,与人臣言则忠于上,于人兄言则友于弟,与人子言则孝于亲,与人友言则信于父,与人夫言则和于室,与人妇言则贞于夫,与人弟言则敬于礼⑨。而《虚皇天尊初真十诫》和《玉清经十诫》等,则具有非常浓厚的儒家色彩。前者云,不得不忠不孝,不仁不信。后者云(引文据《云笈七籤》卷三十八),“不得违戾父母师长,反逆不孝”(第一戒);“不得叛逆君主,谋害家国”(第三戒)。《玉清经》所说二戒,是与洞玄灵宝十善中的“一念孝顺父母”、“二念忠事君师”相对应的。
更广泛而言,儒家有“七情”(人的七种感情或情绪)、“十义”(伦理道德的十个原则)的提倡,道家亦倡此说。《礼记·礼运》云:“何谓七情?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,七者弗学而能。何谓人义?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悌、夫义、妇听、长惠、幼顺、君仁、臣忠,十者谓之十义。……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,修十义,讲信修睦,尚辞让,去争夺,舍礼何以治之?”《云笈七籤》卷一百云:“帝(黄帝)始制七情,行十义之教。七情者,喜、怒、哀、乐、惧、恶、欲七情也。十义者,君仁、臣忠、父慈、子孝、兄良,弟悌、夫义、妇听、长惠、幼顺十义也。”《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》亦云,凡修道之人,“其能壮事守善,能如要言:臣忠、子孝、夫信、妇贞、兄敬、弟顺,内无二心,便可为善,得种民矣”;又特别强调,“事师不可不敬,事亲不可不孝,事君不可不忠,……仁义不可不行”。这也是道教伦理“儒学化”的表现。
由此可以看出,“儒学化”也是道教伦理最突出的特征。诚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,早期道教,除张角、李弘等农民起义所利用的民间道教组织外,其他所有上层道教,都不是作为儒学的对立面,而是作为儒学的辅翼出现的,儒学是他们吸收思想营养的重要来源。如《太平经》强调忠君、孝亲、敬长,《老子想尔注》肯定忠、孝、仁、义,葛洪、寇谦之、陆修静等人更是宣扬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