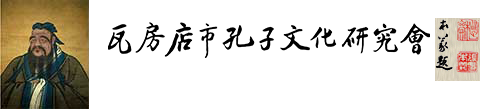儒家的“生死观”
2009-10-02 浏览394次
关于这个话题,肯定有许多人反对,儒家没有谁谈生死呀?哪来的生死观?就算孔子说过:“未知生,焉知死?”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”也没有大谈生死问题。但我们看完儒家经典,就会明白,先秦儒家诸子都是很重视生死问题的。
首先讲“生”,先秦儒家诸子都非常重视生的问题,他们普遍认为,人生一世,必须是要快乐的,而寻求快乐的人生,必须要牢记“仁义礼智信”,按“仁义礼智信”原则行为,才能获得快乐的人生(详看拙作《儒学的人生观》)。所以曾子作《大学》,子思作《中庸》,孟子作《孟子》,等等。这四本书无一不牵涉到人生快乐问题。
儒家们并没有把快乐放到其它宗教所想象的死后的世界里,所以,儒家们认为不存在什么天堂、极乐世界,快乐就在我们的现世现实。这一点颇象佛教的顿悟,当下即是净土,当下即是极乐世界。这一点又象现代科学,死后即回归自然。所以,儒学的生死观是无神论的,“未知生,焉知死?”、“务民之义,敬鬼神而远之,可谓知矣。”说实话,我们连为什么生在这个地球上都没有弄清楚,又怎么能知道死后往哪里去呢?在这个宇宙里,在这个银河系里,是否只有地球能容纳我们,是否只有六道轮回能决定我们去往哪里?是否我们第一次来地球只是出于一时好奇?或是命中注定?不!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,又怎么能了解生死!银河系有银河系的运行法则,地球有地球的运行法则,万物生长在地球上,当然要遵循地球的运行法则;而鬼神就可以不遵守地球的运行法则了吗?当然要遵守!既然鬼神们也要遵守地球的运行法则,我们又依靠鬼神们干什么呢?
孔子为什么说: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”孔子想闻什么道?这个道就是:每天的日出日落,月盈月亏,四季的交替,植物的生长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,动物的出生、成长、死亡等等都各有其独特的道路。大自然由许多小自然构成,诸如人与动物,作物和树木,山与泽,水与火,风与雷,天与地等,这些存在物就构成了宇宙。凡此不同的存在物都有自己的道,就象大自然的情况一样,各自遵循自己的道。普遍性的大道由众多的小道构成,一切此类小道都有其自然之道要遵循,从开始到成熟最后到终点。这个“道”,也就是老子和孔子所描述的“道”。能真正弄懂这个“道”,是很不容易的,如果真的弄懂了,当然也就死而无憾了。
每一个人都是沿着自己的人生道路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的,不能因为没有人看见、没有人听到就偏离自己人生的道路。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,以为没有人看见、没有人听到,便可以为所欲为,肆无忌惮,恣意纵欲;殊不知,你既然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,你自己如果偏离了、走岔了、跌倒了、躺下了,这都是你自己个人的事,不关别人的事。如果有人看见或听到而拉你搀你扶你帮你,这是你的幸事;如果没有人看见或听到,就不会有人来拉你搀你扶你帮你了,你由此也就走不好你的人生道路。而走不好你的人生道路,你就不能获得快乐和幸福。而不快乐和不幸福的生活是谁都不想过的。这就是孔子的思想。
再看先秦诸子他们对待祭祀的态度,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对待死亡问题。孔子曰:“生,事之以礼;死,葬之以礼,祭之以礼(《论语•为政》)。”孔子曰:“大哉问!礼,与齐奢也,宁俭;丧,与齐易也,宁戚(《论语•八佾》)。”儒家慎重地对待祭祀的传统,来源于周文王,在夏商时代,祭祀是由夏王、商王独家垄断,普通诸侯国是没有祭祀的权力的,更何况他们祭祀的大都是鬼、神。自周文王开始,祭祀的权力被争取到小邦国手中,而且祭祀的对象也由鬼、神而转移到人上,也就是说,由周文王开始了对先祖的祭祀和崇拜。这在西周以后人们对三皇五帝的传说中可以看到。《国语•晋语》及《世本》和《大戴礼记》中的《帝系》,都说黄帝是少典之子。《史记•五帝本纪》说黄帝“姓公孙,名曰轩辕”,其国号为“有熊”。崔述《补上古考信录》指出,“公孙”是公之孙,上古时无此称;“轩辕”是指黄帝居轩辕之丘,依所居以为号,非黄帝名;“有熊”不见于传、记,不合《帝系》原意。崔述的批评是对的,但既是神话,亦不需深究其是非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易•系辞》、《世本•作篇》等各种文献都盛称黄帝时期有许多发明创造。属于生产技术方面的,有穿井、作杵臼、作弓矢、服牛乘马、作驾、作舟等;属于物质生活方面的,有制衣裳、旃冕、扉履等;精神文化方面则有作甲子、占日月、算数、调历、造律吕、笙竽、医药、文字等。其中当然有不少是黄帝以后的发明创造,但也反映了黄帝族获得的辉煌成就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,黄帝与蚩尤曾战于冀州之野,以应龙、女魃杀蚩尤。而《逸周书•尝麦篇》则载杀蚩尤于中冀。此所谓中冀、冀州,当均指涿鹿所在。夏族与蚩尤之争还反映在《尚书•吕刑》中,这一由来已久的历史传说,当有史实为背景。《五帝本纪》说黄帝“北逐荤粥”,这是他在进入冀州后,为保居住领域的安宁所采取的必要行动。“皇”的原义是“大”和“美”,不作名词用。战国末,因上帝的“帝”字被作为人主的称呼,遂用“皇”字来称上帝,如《楚辞》中的西皇、东皇、上皇等。时又有天皇、地皇、泰皇之名, 称为“三皇”。 在《周礼》、《吕氏春秋》与《庄子》中也始有指人主的“三皇五帝”,《管子》并对皇、帝、王、霸四者的不同意义作了解释,但都未实定其人名。“帝”原指天帝,人间的“五帝”一词在孟子时尚未出现,他书中只提到“三王五霸”。《荀子》中才有“五帝”一词排在“三王”前,但无人名,只在其《议兵篇》中称尧、舜、禹、汤为“四帝”。《孙子兵法》有“此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”句,似亦有四帝、五帝之称(但梅尧臣谓此“帝”字系“军”之讹)。《管子》及《庄子》所屡称“三皇五帝”,也都未指实人名。其实,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记载神话和历史传说文籍中,先后出现了很多古帝或宗神名号。这些都说明了人们逐渐开始了对人类先祖中杰出人物的祟拜。
何谓杰出人物?即对人类有贡献的人!自夏至商至西周,经历了一千多年,然而人们并没有祭祀和崇拜每一个统治者,只是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的人,人们才祭祀和崇拜他们。那么,为了得到后人的祭祀和崇拜,儒家诸分子更是强调了人生在世,必须要对人类有贡献。“夫仁者,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(《论语•雍也》)。”孔子的意思是,在自己想要立起来的同时也帮助别人立起来,在自己想要做到某些事的时候也帮助别人做到,这样就很不错了,就是一个仁人了。能由自己推及到别人身上,这就可以说是实行人与人相互亲爱的一个很好的方法。也就是说,自己饿了,也要想着别人也是饿的,自己冷了,也要想着别人穿的衣服够不够。在很多事情上都能想到别人,或是在一切事情上都要想到别人,这样的人也就是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,并能寻求到最佳行为方式的人了。而且,这样做并不伤害自己。也就是说,在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同时,尽力帮助别人、成就别人也就可以了。如果是踩着别人的身体往上爬,捞取自己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,损人利己,那就显然是不对的了。所以儒家诸分子大都是不遗余力地奔走、游说,力图挽救社会,挽救民生,力图做社会的中流砥柱。这便是儒家的“生死观”。
《论语•宪问》记载:子曰: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?未有小人而仁者也!”这个意思是说,孔子说:“君子之中如果有不能与人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的有没有呢?没有见过小人能与人建立起与人相互亲爱的关系的。”在孔子所有的论述中,君子之所以称为君子,就是君子必然是能与人相互亲爱的,孔子没有说过君子可以不与人相互亲爱,如果不能与人相互亲爱,“不仁”,也就称不上是个君子了,更谈不上是个君子了。所以,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?”没有!那么小人之中有谁能与人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呢?从表面上看,小人与他们身边的人相处时,也是关系融洽的,似乎也是和颜悦色、和蔼可亲而讲信修睦的。但是,小人们在与人相处时,最怕的就是利益问题,一旦有利害关系,一旦某人没有了利用价值,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质的变化。君子可以损己利人,可以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,可以“贫而乐,富而好礼”,可以“先之劳之”而“无倦”。喜好“仁”的人,不会羞耻于与“不仁”的人交往,既然这个人能够与人相互亲爱,那么对于不能与人相互亲爱的人,他也能够去与他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。后来佛家提出的“大慈悲心”,就是描述了孔子所说的这种心态。就是说,一个人一旦从心底里发生出大慈悲心,他看任何人,对任何人都有一种怜悯的心态,慈悲的心态。唉,这个人真傻、真笨,怎么会做这种事呢?我该怎样帮助他呢?尽管这个人确实够坏,但有“仁”心的人仍然想帮助他。如果说,看见一个不仁的人,你就厌恶他,讨厌他,你没有起码的慈悲心,你的行为能称得上是“仁”吗?平常,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,多数考虑的是“我”自己,我饿了,我累了,我困了,我渴了,我怎么怎么的,能够在一整天的时间里都忘我、无我,这是很难做到。所以孔子说“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乎”,因为这种“于仁”的精力我们每个人都有,只不过我们想到了自己就忘掉了别人。所以,能够在想到自己的同时又能够想到别人,这就很不错了。小人们则是利己后才能利人,或是损人利己,双赢可以,自己不赢而别人赢,那是不可以的。要想损己利人?更不可能!除非在损己利人的后面有更大的利益,也就是说,必须要有更多的回报。如果损己利人了,而回报很少或是没有,那绝对再也不能与他人保持相互亲爱的关系了。做人就要做君子,这就是儒家的人生观、生死观。
《论语•宪问》记载:南宫适问於孔子曰:“羿善射,奡荡舟,俱不得其死然。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。”夫子不答。南宫适出,子曰:“君子哉若人!尚德哉若人!”这个意思是说,南宫适向孔子问道:“羿擅长射箭,奡擅长水战,但都不得好死。禹和稷亲自下地种庄稼,却都得到了天下。”孔子没有回答他说的话。等到南宫适出去后,孔子说道:“所谓君子也就是这样的人了,所谓崇尚正常的人生规律就是象这样的人。”羿和奡有言亦有勇,依靠自己的勇武之力去侵略别人,就是想贪图更多的物质享受,贪图更多的名誉地位,然而最终羿被他的臣子寒浞所杀,奡后被少康所诛,均不得好死。与其不同的禹和稷则是“先之劳之”、“无倦”于稼穑,得到人民的爱戴与拥护而终有天下,而寿终正寝。南宫适对于羿和奡,禹和稷,谁是君子,谁是小人,似乎分辨不出,于是问孔子。对于这个问题,孔子认为南宫适是应该懂的,而南宫适不懂,所以孔子懒得回答他。等到南宫适出去后,孔子才说禹和稷“君子哉若人!尚德哉若人!”这其实也是告诉我们,想要找钱,想要当官,想要取得很好的生存环境,靠侵略、掠夺、剥削别人只能暂时得到片刻的享受,而不能得到人民长时期的拥护,不能长时间地保住既得的所有。而踏踏实实做事,尽心尽力、真心诚意地为大家谋福利,才能得到大家的爱戴与拥护,才能长时期地保住良好的生存环境,才能长时间地保住既得利益。看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,偷摸扒窃、偷税漏税、贪赃枉法的人,有谁能长时期地保住既得利益?有谁能得到好死?虽然有些还没有被正法,但不是不报,时候未到而已。
《论语•子罕》记载:“子疾病,子路使门人为臣。病闻,曰:‘久矣哉,由之行诈也!无臣而为有臣,吾谁欺?欺天乎?且予与其死於臣之手也,无甯死於二三子之手乎!且予纵不得大葬,予死於道路乎?’”这个意思是说,孔子病得很严重,子路就让门人弟子来充当奴仆。在病情减轻期间,孔子说:“我生病这样久了,仲由这小子使用欺骗的方法,我这里本来是没有奴仆的,而仲由用了奴仆。我欺骗谁呢?欺骗天吗?而且我与其死于奴仆的手里,宁肯在你们这些弟子手里死去。而且我死了后即使不能得到大葬的礼节,难道我就会死在道路上吗?”通过这段论述,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家庭的境况。在西周、在春秋、战国时代,稍微有点地位的人,家里都使用有奴隶或奴仆。而且,都是以奴隶数量的多少来互相攀比的。也就是说,我奴隶多,我就富有,你奴隶少,你就比不上我。在这种社会环境中,孔子作为一个鲁国的大夫级官员或是作为一个很博学的大知识分子,家里多少应该是有几个奴隶的,然而实际上却没有!所以,由此观之,孔子在一生的生活中,都是自己照顾自己,也没有象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请个保姆来照顾生活。开门七件事,油盐柴米酱醋茶,都是孔子和家里人自己动手。这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显得很落魄或是显得很贫穷,但这种做法却体现出孔子真正平凡的本色以及他那人人平等的思想。
由于奴隶数量少或者是没有奴隶而使社会地位不高,因而不能享受大葬的礼节,孔子对此并不在意,他相信自己不会死在道路上也就够了。而所谓隆重的丧葬礼仪,只是一个虚名,满足人的虚荣心而已。人都死了,还要那个隆重的礼仪有什么用呢?当然,孔子不是反对举行葬礼,在《学而》与《为政》篇中,孔子多次提到过“孝”,即是在思想上能继承前人之志,而不在于什么隆重不隆重的礼节。礼节只是表达了我们对杰出人物的敬仰与崇拜。所以,这一段是继前面的论述,再一次表现出了孔子普通而平凡的本性与本色。只有将生与死看得很淡泊的人,才会有如此广阔的胸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