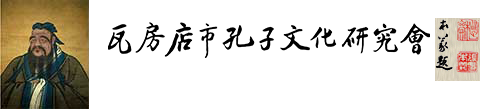专访季羡林教授
2009-07-30 浏览258次
|
| ||||||
|
| ||||||
对于季羡林教授,早在我念中学时就已知晓一二。可当时只知他是闻名遐迩的大学问家,具体情况并不了解。那时,季老在我心里显得神秘而又遥远。当我有幸拜访了季老,让我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…… 简朴生活坦诚心 第一次拜访季老是在去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。当我怀着激动而紧张的心情踏入北大后湖朗润园季老简易的居室时,首先迎出来的是李玉洁老师。作为季老的助手兼秘书,李老师跟随季老已长达五十多年。进入客厅,季老早已坐在沙发上等候我了。 只见他身着灰色中山装,脚上那双黑色布鞋颇有长老意味。噢,这就是我仰慕已久的“国学大师”,这里就是“学界泰斗”的家。 季老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书橱。为给季老创造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,北大特意分给季老两套共六室两厅的住房,外加一个封闭的阳台,可这些空间全都摆满了书橱、书架,就连过道两侧,甚至卫生间也全是书架林立。在数万册藏书中,有一些梵文和西文书籍堪称海内孤本。环顾四周,你会看到桌上是书,床头上是书,沙发上是书,窗台上也是书。已读完的书、读了部分还要继续读的敞开的书、用卡片做标记将要读的书、写了一半的书……这些书都井井有条地放在各自该放的地方。置身于这书的海洋,直觉得书也适意,人也适意。书与人相伴,书欢喜;人与书相伴,人欢喜。季老不仅喜欢买书,而且对书十分爱惜,从不在书上做任何标记,对所需资料全都做成卡片收集起来。因此,他的藏书既整洁又规范。季老一有钱就买书,他把工资、稿费收入的大部分都用来买书,许多次竟因买书后无钱乘车,便背着书走回家。 季老家的书桌和饭桌等都是用了几十年的普通家具。他的饮食也十分简单:早餐一杯牛奶、一块面包、一把炒花生米;午餐和晚餐则多以素菜为主。季老每天都坚持看半小时的新闻联播,可他用的竟还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买的19寸电视机。生活上极其简朴的季老,却将一笔又一笔节省下来的工资和稿费慷慨地捐献给家乡学校,捐献给家乡建卫生院。 季老在母校清华读了4年书,而在北大则工作了55年。当谈及清华与北大各自的风格时,季老形象而又风趣地回答说,清华好比“诗仙”李白,北大则如“诗圣”杜甫。季老坦言两个学校风格迥异,其原因在于两校基础的不同。清华大学创建时,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深;而北京大学始自国子监,再到大学堂,一直是全国的最高学府,对传统文化的禀承使得北大文化积淀深厚,而不足之处就是“封建”的影响多了些。两所学府各有千秋:清华清新俊逸,北大深厚凝重。最后,季老总结说:“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。人类唯有互相学习,取长补短,才能不断前进。北大与清华这‘两个邻家’更应如此。两家相互学习,取长补短,就都又‘仙’又‘圣’了。” 谈起青年时代的求学之路,季老兴奋地告诉我:“当年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我,而我最终选择了清华。之所以选择清华,是因为清华出国机会多。”当问起季老为何想出国时,季老回答说:“就是想出国镀镀金,回国后好找工作。”季老心智之开明,胸怀之坦荡,由此可见一斑。其实就“镀金”本身而言,一些金属物品镀上金后不仅光显,而且耐用,更何况这是季老谦虚而又实在的一种说法。 生命达观大智慧 近几年,季老因潜心研究和写作,对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并不很注意,曾几次受到失明威胁和一连串其他疾病的困扰。2002年夏季,由于皮肤病导致的并发症,使季老曾一度病重,被送进解放军总医院。国庆节时,我去医院看望季老,一进门,只见季老正专心致志地伏案写作。床头、桌上、椅子,满都是书籍和手稿。 李玉洁老师心痛地对我说,季老此次病后,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原本话就不多,现在好几天都不说一句话。每天除了例行的吃药打针,就是看书写字,但即使病危期间也依然乐观。那时季老想到了死,他很风趣地说:“人总是要死的,在这方面谁也没有豁免权。人们有了忧愁痛苦,如不渐渐淡化,则一定会活不下去。人逢喜事,倘若不渐渐恢复平静,也必然会忘乎所以,甚至发狂。人们进入老境也是逐渐感觉到的。能够感觉到老,其妙无穷。从积极方面讲,它能够提醒你:一个人的岁月绝不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,应抓紧时间把想做的事做完做好。 免得时辰一到,后悔莫及。”季老用陶渊明的一首诗作为人生的座右铭:“纵浪大化中,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,无复独多虑。” 关于养生之道,季老信奉自己的“三不主义”,即不误时,不挑食,不嘀咕。所谓“不误时”,就是惜时如金。他认为,人生的意义在于工作,而工作则必须有健康的体魄,健康的体魄则需要体育锻炼。所以进行一定时间的锻炼是必要的;但倘若将大量时间用于锻炼而耽误了工作,则便失去了意义。在季老看来,只要腿勤、手勤、脑勤,自然百病不生。 “不嘀咕”是指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,季老从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,永远保持着平和向上的心态。他说,待人要真诚,不虚假,且能容忍;而对自己则不能疑神疑鬼。“人老了,难免要添点小毛病,没什么可怕的。我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,心里没负担,身体自然也就好了。做到这步就要乐观、达观,凡事想开一些。人的一切要合乎科学规律、顺其自然,不大喜大悲,不多忧虑,最重要的是多做点有益的事。我一生也有坎坷,甚至遭遇过非人的待遇。若不是思想达观,很难想象我能活到今天。” 作为著作等身的语言学家、翻译家,在长达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,季老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四点半起床,五时吃早点,吃完早点就开始写作。在上班族每一天的“正式”工作开始前,季老已做完了一天中他要完成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任务。我好奇地问:“每天4点半起床难道不困么?”他笑笑回答说:“怎么不困?但到时候就像有鞭子在抽,提醒我非起来不可。”这不由使我联想起季老在《罗摩衍那》后记中的一句话:“我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用来工作,我始终不敢放松一分一秒。如稍有放松,静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,好像犯了什么罪,好像在慢性自杀。”惜时如金的季老,其写作效率之高、速度之快,也同样令人惊讶。他那篇脍炙人口的散文《赋得永久的悔》就是季老短短几小时创作出来的。 小处也显大风范 季老之所以被世人敬仰,不仅由于他卓越的学术地位,更在于他不凡的人格魅力。对不平之事,他仗义执言;对晚辈后生,则极力扶持。与他谈话,不论你的身份地位,也不管你学问深浅,他从不会随便打断你,每次都等你说完才会发表自己的看法。 长期以来,慕名找季老写文章、采访、题字的人络绎不绝,每天都有好几拨。工作人员为了季老的健康,有时不免找些理由“挡驾”。一日,北大一位退休的张老师来找季老为他的书写序。工作人员“挡驾”说季老不在,张老师只好悻悻离去。不料屋外的“交涉”被屋里耳聪的季老听到了。不由分说,他从阳台来到屋外,向正在离去的张老师招呼道:“张老师,我在家,你请来吧。”张老师十分惊喜,工作人员却陷入尴尬。季老把张老师请进屋内,接过张老师的书,爽快地答应挤时间为他的书写序。事后,季老对工作人员说:“人活着就是为了对社会有用,我做研究对人有用,为人写序也是对人有用。人家需要,你能做而没有去做,心里会过意不去。” 多年来,有来往的人无论是谁,季老都一视同仁、以礼相待。就连开车的司机他也都能一一叫上姓名。每当司机送他回家,甚至医院清洁工提壶开水,季老也总忘不了道一声:“谢谢,辛苦了。” “为人民多做工作,为社会多作贡献。”已成为季老的人生宗旨。北大人都知道:季老一生没说过任何人一句坏话,即使是“文革”中对他进行过错误批判的人,也不记恨,甚至该提拔使用时,还主动推荐。他说,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错误。犯错误的人知错了就行,你不批评他,他也已很难过了…… 季老还是位做事极认真的人。他所写文章不管多少页,总是工工整整、清清楚楚,没有丝毫的涂改。他说,不然排字工人看起来会很困难。2002年10月23日,北大图书馆百年馆庆,当时正逢季老大病初愈。为他的健康考虑,工作人员决定不让他参加此次庆典。可等到庆典那天,季老早早地便换好了衣服。工作人员善意地向他谎报:庆典取消了。可季老仍旧坚持要去,工作人员只好推辞说事先没安排车,他却说:没车就步行。结果硬是以92岁的年迈之躯提前5分钟到达会场。 “季荷”飘香未名湖 一些了解季老的人认为他是位感情丰富的性情中人。但季老却说自己干干巴巴,宛如一棵枯树,只有树干和树枝,而无鲜花与绿叶。因为自己搞的学问,别人称之为“天书”;自己写的著作,别人视之为神秘。他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在自己枯燥的心田里开出一些鲜花,长出几许绿叶。事实上,凡接触过季老的人无不认为: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人,季老丝毫也不显得枯燥干巴。生活中,他不但重情、守义,而且惜缘。莲花池中的季荷,燕园内的二月兰,居室中的波斯猫,等等,无一不沐浴着季老的关爱与柔情。一日,他平时最爱走的燕园幽径上一棵古藤无故被砍。看到藤萝上初绽的一串串淡紫色的花朵还没来得及知道厄运之信息,依旧像往常一样坦然地在绿叶丛中烂漫地微笑,季老忍不住万斛伤感:“这一串串鲜活的花儿仿佛成了失掉母亲的孤儿,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,最终连痛哭都没有地方了。” 2002年7月14日,大病初愈的季老在约见民办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时,真诚坦露了他对民办教育的理解和支持……表达了对丁祖诒15年来为民办教育拼搏奋争的理解与关爱。出自内心的真情与感动,丁祖诒在当晚为北大学子所做讲演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我拜见了季老,我看到了真正的大海!季老海一样的博大胸怀,既牵挂着为之献身了近一个世纪的国办教育,又海纳着拓荒起步的民办教育。季老对人类、对社会、对民办教育的关爱及内心喷发出的忧国忧民的变革思想,怎不令中国1300所民办高校的200万大学生为之振奋,怎不让我这大海中的一滴水永远奔流不息!”说这番话时,丁祖诒这位来自三秦大地的硬汉子竟禁不住热泪盈眶。 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说:“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,季老献身于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学术事业,取得了杰出成就,成为我国教育界和知识界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。”对此,季老连说:“不敢当。大家把我说得太好了。其实,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,比我学问深的人很多,只是他们先于我而去。” 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说:“季老心中装载的不仅仅是中国,而是整个东方、乃至整个世界。他是为传播整个人类的文化和精神毕生耕耘、无私奉献、闪闪发光。季老的人生原本就是一部书,一部启迪人智慧的书,一部净化人心灵的书,一部永远激励人奋进的书,一部令人回味无穷的书。” 是啊,随着岁月的沉淀,季老那看似沉静实则饱蘸激情的人生不但没有丝毫的枯萎和凋谢,反而愈发泛彩流光、愈发富有魅力。蓦然间,我分明看见:季老的心田生长出了一片片如荫的荷叶,那一片片荷叶中又盛开出一朵朵绚丽、圣洁的荷花。 相关链接 1911年,季老出生于山东清平县一个农民家庭,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德文,1935年考取赴德研究生,入哥廷根大学学习佛教梵文、吐火罗文及巴利文等古代语言。后因二战爆发滞留德国长达10年。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。1945年,谢绝了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,辗转瑞士、法国、越南、香港,于1946年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,并创办了东方语言文学系,开拓了我国东方学学术园地。即使在“文革”那样艰苦的条件下,他仍着手翻译了印度史诗《罗摩衍那》。八十年代,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构建全民族人文精神素质,他主持编纂了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、《传世藏书》、《神州文化集成》及《东方文化集成》等大型丛书。在吐火罗文研究、印度佛学、东方文化、比较文学、唐史研究及中外关系史等广泛领域均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尤其是《吐火罗文》一书,是季老85岁后用英文冲刺的作品,其学术价值极高。 |